ժҪ���^ȥ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δֹͣ�^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ԑ������ʮլ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ȕ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?x��)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[��϶�g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Ⱥ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ŗ���϶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׃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g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��ث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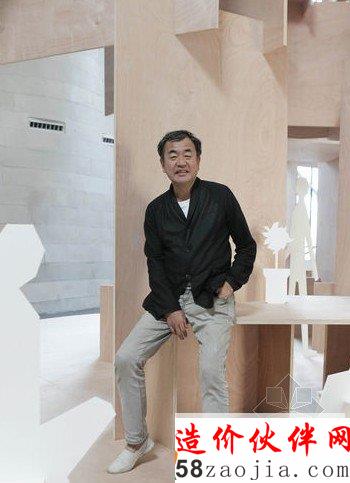
�DƬ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o�i��ü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ݵ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ǡ�3��11���𡱺�Ĕ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ʹ���ְl(f��)����ʡ���R�^�ڗ��օ^(q��)��S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@�C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g����ѭ�h(hu��n)���š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3�Ї�չ��϶�g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^�֖|�͗��ֵăɂ����^�e�С�����f��δ��ɵ��@���o(j��)�ƬƬ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c��һͬչʾ�Ľ���ģ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ˮ߅�Ļ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ˮ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ƽ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ľ�|(zh��)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7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uՓ��ӛ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Լ��ڵ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@ЩҊ�Զ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ľ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ěQ�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IJ��H�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ĩ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Σ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ķ��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ġ�9��11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3��1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ȥ1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Г�(d��n)��һ�δεĚ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����ķN�N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Ľ����ĽǶ��ṩһ�N��Q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ǣ��^ȥ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δֹͣ�^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լՓ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ȕ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?x��)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[��϶�g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Ⱥ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ŗ���϶�g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g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��ث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[���]�гʬF(x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M(j��n)�е��(xi��ng)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õ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f�\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ľ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Ї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Ҳ�H�и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Ļ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ӌ�Сľ�ݯB�Ӷ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^ȥ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픿���ʹ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Z�R�ڮ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Ҳ���Ì���(y��ng)�˜\������߅�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Ы@�õ��`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ڱ���չ�[��Ҳ��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˖|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Ы@ȡ�˲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Ї����ձ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ą^(q��)�e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ձ�һֱ�ԁ팦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l(f��)չ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Ҳ��һЩ�µ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µĺ����ԣ���˷dz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ÿ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Լ��ܵ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ٻص��ձ��r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��_ʼ̤�뽨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ձ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ĭ�Ɯ���^�̡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Ї�ͬ��̎�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d��ľ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ͬ�ӵĆ��}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Ġ�B(t��i)�ͬF(xi��n)�ڵ��Ї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���ձ��˶����Ҫ�I�Լ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ס���w��ĸߘǴ�B����X�@�Ӳ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@�ɟᳱ�^ȥ���ձ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µĸ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_ʼ�����µ��B�ӡ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ѬF(xi��n)�ڵ��Ї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һЩ���Ƶ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ľ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Щ��ͬ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R߀�]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Ƕȁ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Г�(d��n)�Ěvʷʹ���Ȯ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(xi��ng)Ŀ�����Ҳ�dz���ҕ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
Q���㌑�^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ķ��g��Defeated Architecture(ʧ���Ľ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ڮ�(d��ng)�r����һ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XЧ���ăA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ڡ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(j��)��ͬ�ķ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ȡ�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һ�I�����^ʧ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ĸ߶ȡ����۶ȁ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^ʧ���Ľ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Ӫ�(d��)�ء�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ĽǶ�ȥ�A�ø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ý�İl(f��)չ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Ľ����@���˳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N����߅�h(hu��n)���Џ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İl(f��)չҎ(gu��)�ɡ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N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к�(qi��ng)�ķ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˃�(n��i)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s�ⲿ�Ķ��Э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ڸ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õĽ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N���m�ϵĽ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С�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㲻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Ї��M(j��n)�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]���X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ֵ�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ܵģ�
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Ă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РI����ķ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һ�N�Єӡ����K�ݵĈ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ʌm��߀�б������ĺ�Ժ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ȥ֮����X�䌍(sh��)ͦ�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ķՇ��s�˸е��dz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�3��11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Л]��һЩ�µĸ��ܣ���չ�[���Л]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ͨ�^�@�Ξ�(z��i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ܵ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҂�����ҕ��ʧ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Ȼ��ͨ�^�@�N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ď?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˞�(z��i)�^(q��)���ܶ���ˮ߅�Ļ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ˮ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ƽ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ľ�|(zh��)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ܕ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µČ�����ď�(qi��ng)�ݺ͈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ʲô�ط���ʹ��ʲô���ϣ���ô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f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Ҳ���^ϲ�gľ�^���ľ�^�ǖ|���Ă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S�o(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õñ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㿼�]�^���ľS�o(h��)���Թ̆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ȃ?y��u)�ݫ@���ˏV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ָ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܈Թ̣��sȱ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ȱ��϶�g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¼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M(j��n)չ����ľ�^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Ȇ��}���õ��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ľ�콨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ā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@�����玧���µ��@ϲ��
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Ʒ��ʮլՓ���ԑ��o�ķ�ʽ�O(sh��)���˸���(j��)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Nס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չ�[�еġ�SHARE HOUSE��(����סլ)�Dz����㌦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ʮլՓ���r����˂�ע�ذl(f��)չ˽�п��g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ʽסլ�dz��dʢ�����Ү�(d��ng)�r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@�N˽��סլ�ͼ���ʽסլ���g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SHARE HOUS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g�ͷ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SHARE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Ъ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g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ں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@�N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Ԍ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һЩ�e�O���Ƅ����á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Ľ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İl(f��)չ�o���µĴ𰸡��@��չ�[ϣ���ԡ�SHARE HOUS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o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R֮ʿһЩ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ҕ��е��dz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�SHARE HOUS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ᘌ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څ�ݶ��Եģ�
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g��څ�ݷdz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ڸ��ٰl(f��)չ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ܵ��W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ϣ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˽�ܿ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˿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˺ܶ��@�SHARE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ȸ����O(sh��)ʩ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Լ���˽�ܿ��g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ҹ�ͬ���c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څ�����ձ��dz��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ᘌ�ԭ���ļ�ͥ���ѵ��ˆ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M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��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˿چ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SHARE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ܕ��o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e�O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߀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@����Ƶ�ģʽ���ձ�߀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Ԍ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��g��ֲ���M(j��n)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\(y��n)�õĶ��Ǻ����r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@�Nƴ�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Թ�����ȫ�]�І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һ�N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Ľ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@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
Q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͕����ľ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
 ��
��
 ��
��